 耳边永远垂着耳机的城市游民们打从Walkman出现之时就已经重塑了都市的声线。几年前, Mark Shepard 建议人们超越这种自播(egocasting) 态度,把声音分享给路过同一空间的他人。他的作品叫做Tactical Sound Garden,在全世界多个艺术节和活动上进行过展示,从巴塞罗那的 Sonar 到San Jose的 ISEA 2006,曼切斯特的Futuresonic 一直到纽约的 Conflux。
耳边永远垂着耳机的城市游民们打从Walkman出现之时就已经重塑了都市的声线。几年前, Mark Shepard 建议人们超越这种自播(egocasting) 态度,把声音分享给路过同一空间的他人。他的作品叫做Tactical Sound Garden,在全世界多个艺术节和活动上进行过展示,从巴塞罗那的 Sonar 到San Jose的 ISEA 2006,曼切斯特的Futuresonic 一直到纽约的 Conflux。
不过,TSG只代表了Shepard的一小部分活动。他的艺术实践“跨领域实践运用建筑、电影和新媒体来处理全新的社会空间并象征化了愈演愈烈的当代网络社交文化结构。他的研究关注移动与渗透技术对建筑和都市化的影响。他目前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建筑与媒体研究系助理教授,并共同领衔该校的虚拟建筑中心。”
你的简历上说你是“艺术家与建筑师,跨领域实践运用建筑、电影和新媒体来处理全新的社会空间并象征化了愈演愈烈的当代网络社交文化结构”。你认为建筑、电影和新媒体师三个不同的领域,或者你的作品把他们练成了一体?
我的作品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穿梭。我是建筑系出身,过去的二十年里(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学习与实践。90年代初对建筑“职业”感到厌倦以后,我回到了学校学习电影,用电影作为媒体和概念模板来处理空间经验的各个方面,并选择逃开了传统的建筑学表达方法。
从一开始把时间和持续性当作“材料”(声音,灯光,动作的质量)来看待的天真兴趣,一直到更广阔的,对人的注意力是如何建立在技术仪器周围的关注。我对作为都市环境中一种限制状态的空白,以及如何构造各种力量来产生这种状态产生了兴趣。这个作品探索着经验表达的限制,以及建筑师和城规师对一个特定地点的观察和判断上实际上受着他们本身表达能力所限制的事实。Between Now and There 和unfoproject 是两个例子。在电影和建筑中游走(并扩展到影像和都市主义)提供了我对技术,环境的投射与构成,以及这种构成对居民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和批评。

unfoproject
几乎同时,我开始接触新媒体,主要是非线性,暂时结构和互动性。一段时间以后,我与Carlos Tejada一起创建了一个新媒体工作室,叫做dotsperinch。它一开始是一个用来支持独立艺术作品(通过给其他艺术家和设计师自由工作)的渠道,后来成为了艺术家、建筑师、程序员和技术人员在新媒体环境中进行合作的网络,主要为纽约艺术、设计和教育领域中的非赢利组织工作。许多早期dotsperinch的工作是为博物馆设计和编辑在线数据档案和互动展出。像365degrees.org, SonicMemorial.org和CrossingTheBLVD.org都给后来的概念化设计中的数码档案和公开内容系统提供了技术基础。后来的作品,像Mitosis: Formation of Daughter Cells,A.M. Hoch为Beall Center for Art and Technology所做的装置作品,探索着一种“可栖息影院”的概念,创造了一个声音,移动影像和移动观察者的综合体,采用得则是感受器以及内置的微型控制器。
我目前的作品更关注把计算作为环境,而非工具或者一系列的技术来看待。当计算智能越来越内置于(或甚至散布在)已建成的环境当中,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基础就会完全改变。这在当下的大城市里已经不能再明显。观察移动技术和普遍计算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习惯的那些范畴划分,公共/私人、个人/大众、内部/外部、注意力/分心、虚拟/真实。我发现我们必须不断游走在它们之间才能抓住要害。

你的Tactical Sound Garden 已经持续了许多年,这个项目是怎样发展和演变的?
Tactical Sound Garden [TSG] 工具盒从2004年开始成为了一种概念化的产品。可参与声音环境的想法是dotsperinch曾经在2002年的sonicmemorial.org里尝试过的。后来我们发展了一些对定位更敏感的项目,比如The Rosemary Initiative,探索着当代追踪技术对社会互动的影响。2004年春天,我和 Fiona Murphy一起刚刚为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Maya Lin广场完成了一份计划书。Maya Lin给广场的计划是要把声音装置内置于景观里的各种雕塑元素、灯光环境和公共长凳里。我们受邀提议了一系列的方案,来完善她的内置技术计划。“种植声音”的概念直接从那份提议而来。
早先,我与正在进行一个 “Where-Fi”项目的Marc Tuters取得了联系,他用802.11(WiFi)无线接入点在物理空间当中计算位置。Marc介绍给我Placelab,西雅图的英特尔研究所开发的一个开放资源API,与Where-Fi的设计理念许多不谋而合(后来他们成为了这个项目的投资方!)。从那里开始,一个新的程序发展了出来,能够把Placelab当中的定位信息发送到一个3D声音引擎里,根据参与者的地理位置导出实时混音。
现在的互动方式是从低科技的附带日志本的手持广播发送器进化而来得。从这些早期的研究里,我们对哪些变量对人们倾向于(或不倾向于)与周遭环境进行声音互动产生作用得到了一些粗略的印象。虽然作品从真实都市社区花园隐喻开始,虚拟的声音花园却不需要局限于这些变量。比如,社区花园经常围绕着一些“情节”而来,因为一个都市公共空间在空间上是由人们所属的特定团体而划分的。TSG的非物质性,以及它的公共参与模式导致空间划分通常只是TSG的所考虑的各种变量当中的一种。我们通过与一些社会团体合作发展声音花园来继续探索这些变量。我们的想法是要通过共同分享公共空间来构成社会团体——比如机场、公园、街道和广场——而不是由分享住地、财产、兴趣或者信仰来构成。从这个方向来看,这个作品想要创建一种跨过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社区,一个植根于使用日常生活当中的公共空间的多样化社区。

Tactical Sound Garden 要求听众对别人种植的声音给予一定的尊重。你怎样处理这个网络的脆弱性?人们通常怎样反应?他们是不是会去修改别人种下的声音?有没有过争执?或者人们更倾向于合作?
这完全取决于参与的人群和互动的时间长度。一个TSG的互动时间最好用周,月(或者年?)来计算,而非分钟和小时。比如,当我们在ISEA2006 | ZeroOne San Jose Symposium and Festival展出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星期的时间长度很有问题,因为它强迫选择参与的人们有一种“试探”的心态。很多人更倾向于试试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而不是真正参与到互动之中。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自己植入的声音并没有多少投入,也不在乎别人事后怎样修剪。当更多的声音花园持续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人们是怎样互动的。这可还是个棘手的问题。
城市规划者对城市的听觉层面给予足够重视了吗?如果是,可不可以举例说明?如果没有,你认为可以怎样改变?
现代城市里的声音是极度难以控制的。通常来说,城规师更关心为什么城市过度喧闹与嘈杂,并试图用标志和法规来控制声音。汽车喇叭、警鸣、疏忽的用户留下鸣响的汽车警报器、超大型的汽车立体声,建筑工人用冲击钻修理下水道,或者耳背的老年邻居把电视机开到最大声——每一个都有条例或环境影响研究(有时由邻居所做!)来管治。所以想一想,重要的并不是城市规划者是否已经给予了城市的听觉层面足够的重视,而是从一开始,他们是怎样思考城市声音这个问题的。
移动听觉设备,比如iPod,给了普通的城市居民改变和控制自己城市声觉版图的方法。iPod的流行程度指向了一种新的,用自己的声轨个人化城市体验的方法。在公共汽车上,在公园里,在午饭时,在买三明治时——城市好像是一部电影,由你来为它谱曲。这些设备同样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私密性,让听者逃离约定成俗的公共空间互动方式。像Michael Bull在book on the subject 里 所写,挂上一对耳机赐予了你一种社会执照,让你能够在城市中自由移动却并不介入,又赦免了你对周遭发生作出反应的责任。有些人用耳塞来转移不被需要的注意力,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回答任何问题,因为他们看上去已经非常忙碌。另一些人在与别人说话的时候才摘掉耳塞,好像一个信号来告诉别人现在他希望参与。事实上,iPod已经成为了在公共领域当中组织空间,时间和边界的工具。
所以今天,我认为用个人之手来塑造城市听觉体验比相信那些专业城规师要重要的多。毫无疑问,这也可能把城市居民封闭在了自己的空间当中,抽离出了都市公共空间以及当中的社会互动。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城规师可以做的是发展新的科技和基础结构来重新联系人们,塑造一种私密性和开放性共存的日常生活社会空间(而并不一定是公共空间)。
你是建筑与定位科技( Architecture and Situated Technologies)的组织者之一, 这是一个“将艺术、建筑、科技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带到一起,来探索‘定位‘科技在当代元都市生活的设计和居住中日益重要作用的研讨会“。这个活动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科技是怎样在社会中产生作用,包括(非)影响性给予,推翻业已定型的消费者作为使用者的方案等。这个活动有没有让这个问题更清楚一点呢?参会者对此的观点是什么?

我与Omar Khan 和 Trebor Scholz 一起组织了“建筑与定位科技论坛“。这个论坛是虚拟建筑中心(Center for Virtual Architecture),分布创意组织(The Institute for Distributed Creativity),和纽约建筑联盟(Architectural League of New York)的共同产物,也是联盟125年年庆的一部分。
我们对发现对汇聚建筑和定位科技有所帮助的新的研究向量,实践场地以及工作方法都十分感兴趣。我们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后学科的环境里想到这点,并把相关却又无关的人带到一起的呢?如果普遍计算使得计算机退到了后台的位置,变得不可见,并让我们得以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空间,那么什么样的技术-社会相似 性还可能存在,或必须存在?我们怎样找到它们?怎样掌握它们?谁来设计,又根据怎样的标准?
我们从“定位“的两种用法作为出发点:
1.定位:置地:定位于一个定点或位置,“身处高价的都市中心”,“战略定位导弹”,“山顶上的一所房子”,“处在河边的幽静地点”。
2.定位动作:每一个动作过程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材料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每一刻都正在进行的互动过程,每一个动作者之间,以及动作者与环境之间时刻进行着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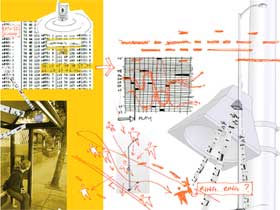
一个问题引发了很多与会者的回应,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样使用不同的移动,内置或者普遍技术来推翻业已定型的消费者作为使用者的方案。英特尔研究所Urban Atmospheres的Eric Paulos展示了Objects of Wonderment (video),一个手机用户可以根据一定的方案,在特定的条件下依照个人需/求/欲望自己设计程序的平台。
Usman Haque的讲话“公共空间里的科技与用户:什么出了问题?”认为用来讨论技术-社会相似性的语言本身就有问题。他展示了一系列能够使用户成为参与者,技术成为工具,公共空间成为共同点的项目,并引发了一个怎样找到更好词汇的大讨论。我们现在正在podcasts所有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整理一些谈话,收看以后你会对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
A&ST也邀请了艺术家就定位科技发表看法。你认为艺术家对技术问题的贡献能有多大?他们的作品和观点怎样能被引入讨论?你的意见是否很难被艺术圈以外的人理解和采纳?
我认为艺术家在科技发展当中的作用是关键的。
他们就科技所提出的问题经常是那些公司研究实验室无法问出的,而这些观察对计算机专家和工程师并非显而易见(至少不是一目了然)。这不是新鲜事了。艺术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对科技的发展作着贡献,像Xerox PARC或者Paul Allen的Interval研究实验室就是两个技术工业的大玩家寻求艺术家帮助他们用更有发明性,更相关的方法思考未来技术的例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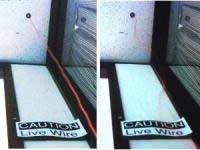
不过他们的意见有没有真的被听进去则是另一个问题。Natalie Jeremijenko ——她的作品Live Wire是当她还在Xerox PARC当研究员的时候开始做的,Mark Weiser和John Seeley Brown在1995年的文章《设计抚慰技术》(Designing Calm Technology)当 中引用了这个作品,但在后来的研讨会上有人告诉我Weiser之后的实验室主任认为这个作品是个“耻辱“,并把它从实验室里清除了出去。她在发言的时候说, 在艺术家只是能够熟练地设计出计算几种物质或者社会情况的操作方案,却不能够用数值标准来测试方案可操作性的情况下,要去影响超越艺术+科技的其他领域, 比如计算机专家,资本投机者,以及其他以技术发展为驱动的商业兴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有一个作品,Industrian Pilz似乎非常有意思。它用细菌镜头观察东德的工业化进程——霉菌的植物学研究。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项目吗?这个想法从哪里来?
Industrian Pilz 从1998年开始创作,是受邀向Areale99电子艺术节提交的一个创意。这个艺术节定位在柏林外围一个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工业区,这个地方曾经是东德的农业区。作品分两个部分。 “pilzcontainer“装置是以一种“移植”的方法设计,它用一个特定场地,电脑控制的装置来表现工业制造和分放的循环过程,并实时与最近的高速公路的交通流进行互动。\\\\\”pilzfilm“, 一个数码录像电影则探索者漂浮在西德吸收东德过程当中的那些被抛弃的残骸,通过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叙事方法纪录了工业区的变迁,把现场拍摄的片断与史料电影、大众媒体对文化全球化的报道和先锋派霉菌美学家约翰·凯奇的音乐交织在一起。它2003年11月在瑞士Basel的Viper国际电影影像节上首映,后来在纽约的Anthology Film Archives放映。
最初的想法是在我98年去工业区实地探访的过程中出现的。我住在与之相邻的一个镇上,每天骑自行车穿过树林来往于工业区。当我骑过那些树林的时候,我不断看到人们貌似漫无目的地行走,低着头仔细观察森林的地面。一直到几天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在采蘑菇。所以我想我自己也要试一试。采蘑菇有意思的地方是,你必须培养出一种好眼力来定位森林里那些可供真菌生长的地点。其他真菌学知识还包括找到确认蘑菇是否有毒的视觉线索。它们可能会是味道鲜美的食物,但如果不小心,也可能让你生病。蘑菇根本不需要太阳。它们靠森林里死掉或者腐烂的东西存活。当然围绕它们的还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神话学 ——毒蕈,神奇环或者这些东西。

Pilzfilm剧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隐喻,正好可以描述把前东德的农业区改成机器工业区,(然后)支持当今柏林(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语境里,真菌学变成了一个转矩,来平衡人们通常以为完全相对的良性,创意型文化和残酷文化。当资本主义所声称的绝对自然性得到了一定的修辞力度,真菌学镜头定义了“自然的几种法则,它可以同时是腐败物的转化,以及一种寄生虫性的,潜在有毒,并且深处以特定场地为中心的过程——它在经济当中的奇特存在不可能用简单浪漫的标志来认识。你最好看看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
你最近正在忙些什么?
在去年秋天赫尔辛基,Weimar和纽约一系列颇有成效的讨论以后,对我而言是回到工作室的时候了。Usman Haque最近寄给我一些他自己environmentXML项目的代码。所以我会钻研一下这一方面。这就好像是为你的数据流而建的Flicker。我觉得它为物质与空间的大规模互动创造了一个开放,可参与的基础结构,也是目前最有前途的追求之一,为都市生活的其他部分打下基础结构。我也在启动一个新的TSG,将会在今年春天和夏天进行一系列工作坊。除此以外,每天回到早上醒来时的那个甜蜜位置,思考前一夜有过的想法,以及(希望)能够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产出一些果实。。。
谢谢Mark!






